时间:2018-10-23编辑:文二
1949年5月13日上午,在南京西康路18号的美国大使馆(今西康宾馆)内,一场特殊的会晤正在进行。会谈的发起方是72岁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
在这次带有试探性质的会面中,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华府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将逐步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并计划把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存放于上海的棉花、面粉等物资移交给中共方面(待上海解放后)。
但在黄华提出的“断绝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一事上,司徒雷登宣称:目前国共两党各占据中国一部分领土,新的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按照国际法,只有在新的、有能力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组织出现之后,美方才会考虑断绝与旧政权的关系、承认新政权;在此之前,华府不会公开声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

关于新政权的构成,他本人希望其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为中国人民所拥护”。黄华直截了当地表示,组建新政府一事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方若有诚意,应首先撤退尚留驻于青岛的舰艇和海军陆战队。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傅泾波一行8人由南京飞往冲绳,历时两个多月的中美密谈最终无果而终。
《黄华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据周恩来透露,1949年6月,司徒雷登曾委托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给毛泽东、周恩来带去一则口信:如果新政权愿在美苏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愿一次性给予新中国5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其恢复经济。
作为对比,1950年中苏结盟之初,苏联对华提供的经济建设贷款仅为3亿美元。巨大的差值使一些批评家不禁质疑:既然连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也曾把中国称为“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1949年时的新中国为何不选择恪守中立,依据现实主义原则从美国谋求实惠的经济进账?中苏结盟,在当时是不是对新中国最有利的外交抉择?
以狭隘的经济算计臧否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大方针的合理性,显然忽视了与生俱来的革命属性之于中共对国际问题认知的决定性影响。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使中国革命与世界反帝斗争的潮流相结合的立场就已成为全党的基本共识。

俟“冷战”爆发,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更印证了这种二元对立观念的合理性,并促使中共领导人扬弃过渡阶段的“中间地带”假设,自两大阵营中择一而处。比较之下,尽管美国一度开出看似慷慨的援助条件,但其基本的战略经济和战略地理假设,与中国急欲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愿景相去甚远。美方对中国新政权构成的一再“关心”和插手,动机更属可疑。
有鉴于此,在1949年3月闭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已提出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三项主要原则;并在当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申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方针,至此尘埃落定。
随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进入1942年,中共领导人开始接受一种带有折中性质的“新秩序”理念。在毛泽东发表于1942—1946年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他将这种“新秩序”描述为:在国际层面,通过“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共的目标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在这一考虑下,抗战结束前后,中共曾尝试与美国政府开展外交接触,并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重庆谈判。
然而,随着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以及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再度开始强调其根本的革命立场。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度将中国称为“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
这一表态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暗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受美苏关系的左右;即使是在莫斯科希望避免对美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共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也不必然导致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中国革命,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质。
其次,它将“中间地带”革命的走向视为更大范围内两大阵营新斗争的序曲,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越是来得迅速,全球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和平的潮流越是能得到助长,从而有助于挫败美国发动新的全面帝国主义战争的潜在可能。

一年后,美国正式介入希腊内战,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划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Strategy of Containment);中共对两大阵营对立的初始判断,再度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194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边倒”这一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这一表态不仅明示了新政权的外交倾向,连带指出了新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移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2月初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期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共在历史上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并反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加强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一边倒”的基本立场之外,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项外交实践领域的原则。前者指的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
后者则是指“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地位。
一个相当微妙的事实是:在对1945—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回顾中,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其国务卿马歇尔的决策,在国共两党方面收获的几乎是毫无二致的批评之声。中共在经历过1949年夏天的秘密会谈之后,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并无诚意,随后开始全面践行其“一边倒”原则。而国民党政权及其在美国的同情者则指责马歇尔等人应当为“失去中国”负责,认为后者未能尽全力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这其中实际涉及两个问题,即: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当司徒雷登获准与中共代表展开接触时,美国究竟愿意为争取新中国恪守中立投入多少资源,承担多大的风险?
答案或许可以自马歇尔的重要智囊、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乔治·凯南在1947—1949年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得出。在凯南看来,即使是在美国已经赢得“二战”、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背景下,不分轻重地滥用战略资源依然无助于确保美国的安全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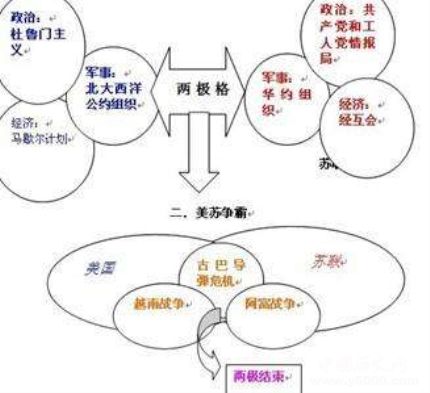
在冷战成为定局的背景下,最具性价比的对苏遏制政策不是漫无边际地挥霍人力、财力,而是牢牢盯住北美、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五个战略地理中心,特别是避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中间地带”国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在日本基本由美国独占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恢复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工业基地的正常运转,从而重新启动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均势机制,抵制苏联影响力的渗透。
依据这一判断,从1948年开始,美国启动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在4年时间里向西欧“输血”170亿美元,使其工业产能获得全面复苏,在对苏遏制战略中先下一城。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华府在事实上接受了优先扶植工业国、首先在欧洲展开对苏“冷战”的方案,则其在中国所愿投入的战略资源总量以及介入的力度当然也会受到显著制约。1945—1947年,美国给予国民党政权的全部经济援助总额为14亿美元,仅相当于欧洲的零头。
在西欧优先、效费比优先的原则指导下,很难想象杜鲁门政府刚刚否决了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倡议,却会慷慨地将5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给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事实上,在1949年7月14日呈递给国务院的未来对华政策评估备忘录中,司徒雷登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必须使中国感到它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关系的必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求程度。”换言之,美方从一开始打的就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算盘:一方面以巨额贷款作为诱饵,要求中共领导人就不会倒向苏联一事做出保证,从而给莫斯科的亚洲战略制造混乱;另一方面随时准备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以便唤起新政权内部的反对声浪,使后者陷入分裂。
寻找并扩大新政权内部的分歧、甚至扶植潜在的美国代理人,从一开始就是杜鲁门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在7月14日的备忘录中,司徒雷登直言:“在目前条件下,要应付中国的难题,最理想的方式是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由中共占1/3,民革占1/3,其他民主人士占1/3,三派各有权力与责任。如此计不成,则应退而求其次,增强非共产党人士在共产党支配之政权内的实力。”
这也是他在和黄华的谈话中屡次提及新政权的“构成问题”的动机。毛泽东对此早已了然于心。在1949年1月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公开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变为“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

在黄华—司徒雷登会谈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外事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曾多次指示:关于司徒雷登北上一事,无论其最终是否成行,均应澄清其“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并且中共高层“对美帝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1948年12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报告了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雷文和在当地的一次谈话,其中提及:美国国务院正寻求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就一个“有效的反对派”,为此将利用当前留驻中国之外交和新闻人员,与民盟和其他中间人士做广泛接触。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批准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人员和记者进入解放区,对滞留的美国外交、军事和新闻人员也仅视为普通侨民,对其行动予以监视,防止其进行宣传、刺探和煽动活动。按照毛泽东在1949年初的说法,“不忙与英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不论是我们承认他们,还是他们承认我们”。
应当指出,在“冷战”初期美苏争夺的重点集中于欧洲的大背景下,整个解放战争中前期,苏联给予中共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量相当有限。当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了苏联在外蒙古和旅顺、大连的利益之后,莫斯科明确认可国民党当局为中国的合法政权,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9月30日。
由于顾虑美国可能直接介入,直到1948年,斯大林才含蓄地承认自己误判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并批准为东北解放区提供基建和交通支持。
1949年7月1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文章,公开宣告中国革命在国际事务中将采取“一边倒”的立场,“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在南京,沮丧万分的司徒雷登被迫承认:“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边,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则无以复加。”大使阁下随后开始打理行装,但他的目的地已经不可能是北平,而是太平洋另一侧的美国本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同一天,根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并亲笔签署了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2月14日,经过长达近三个月的曲折磋商和谈判,中苏两国代表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署了有效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当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对中国而言,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可靠的外部对日安全保障。苏联承诺在1952年底之前将中长铁路(中东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交还中国政府,并从旅顺撤出苏联驻军(实际延迟至1955年)。苏联还同意一次性给予中国12亿旧卢布(合3亿美元)的经济建设贷款。
与不久前莫斯科给予波兰的18亿卢布贷款相比,这不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但对当时的新中国而言,中苏正式结盟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价值,“一边倒”由一种主观意愿变为了既成事实。
在朝鲜战争引发美国进一步建设亚洲“反共堡垒”、新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自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酝酿被称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对外政策,力争扬弃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扩大和平中立趋势,推广和平中立地带”,优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安全缓冲带。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公开指出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标志着新中国开始超越单纯的“革命外交”思维。1953年底,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他正式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国与国之间的共处原则,并在次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付诸实践。
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自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